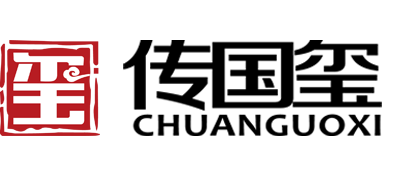两个月前在喜马拉雅上购买了一档意外艺术栏目,总共60期节目。从原始社会的石洞壁画到近现代的意象派、后现代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、立体主义等等。给了我一次非常震撼的艺术之旅(我这广告打的也没谁了)。这一段时间重新回头听第二遍。正好这段时间熊逸学院讲国学,讲到了“诗”。我便对熊逸老师所讲所述越发的好奇。因为众所周知诗至少算得上一种中国古代文字的艺术了。正所谓“英雄见英雄,惺惺相惜”,我倒是非常想感受一下这两种艺术在我这里的对撞。
当然和熊逸老师相比,相形见绌。她老人家能够学到、说到、做到。而我也只能先做到认真的学了。不过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,好东西自然分享一下更让人喜悦。姑且就允许我总结一下吧。
诗正式进入《诗经》之前,在社会中的作用就一个,那就是“淫媒”。如果这个词语你觉得晦涩难懂,或者觉得有错别字,那我再来解释一下。没错,和你想到的一样,最初的诗歌就是用来直指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和欲望,唤醒男女之间的生殖繁衍的欲望。在所谓的民智未开的蛮荒时代,诗歌不是什么艺术,是一种巫术。
在诗歌萌芽的时代,诗不是属于哪个人的,它属于群体,是一种仪式语言。用来通神、敬神。有韵律的诗歌有着一种催眠术的魔力,让诵读诗歌的人获得舒缓和释放,让群体进入一种可控的狂热状态。在反反复复的吟诵中,群体的凝聚力获得巩固,大家感情得到加深。而对于那些适龄男女来说,感情深刻交流的时刻很容易就发展出了眉目传情,最后直奔“不可描述”的事情去了。
熊逸老师指出现代社会中仍然保留着这种原始诗歌的影子。比如铿锵有力的演讲中,加入押韵的排比,便能够很容易的剥夺听众的理性思维,直接将听众引入自己设定好的情感世界。运用这个最好的,当属传销组织中的“领军”人物了,他们只需要在演讲中加入少许的诗歌表达方式,就很容易让他的“教众”抛开一切理性的情感。要是再多一些节奏感强烈还押韵、有涵义又朦胧的句子,那就“如虎添翼”、“锦上添花”了。
古代诗人辈出,经常有人自诩诗歌是有神性。大概就是上述的意思吧。诗歌带给我们的体验,正是原始巫术带给我们的体验。不一样的是,巫术只存与原始蛮荒,有了文明,仪式就不再重现了,而诗歌却独自存活了下来。但是由于被人为的去除了一些,虽然诗歌还活着,但注定不完整了。所以诗歌的发展总免不了被各种政治、经济中的实用主义定义为虚无的缥缈,甚至毫无意义,最后沦为了漫无目的“语言放纵”。无怪乎王安石变法,变得就是去除诗人写诗来治国的尴尬,所谓“百无一用是书生了”,这里书生也可以叫做诗人吧。
这和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还真是颇为相似。从“意外艺术”中学到,艺术的最初原始功能,就是住在洞穴中的原始部落,打不过凶猛的野兽,抓不住体力和耐力远胜于人类的猎物,于是愤恨之际在石洞上画上野兽和猎物,再画上人类带着武器杀死他们。这种感觉颇有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中那个吃喝玩乐为职业的懒羊羊了,一副“画个圈圈诅咒你”的感觉。比如法国的尼奥洞窟、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就保存着最原始的艺术。我选了一个图片在上方,大家可以揣摩一下。
随着历史的发展,艺术开始从实物脱离开来,开始描述各式各样的神话。像布歇的《宙斯与凯利斯特》(下图)和克林姆特的《黄金雨》。给世人展示神话故事,声情并茂总好过口口相传。可是随着神的地位开始下降,人地位的提升,人文色彩开始隆重登场,人就取代了神。所以从文艺复兴三杰开始,达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、米开朗琪罗的大卫、拉斐尔的《西斯廷圣母》就应运而生,再到后来艺术就从完美的人体剥离出来,从具体的现实形象剥离出来,所以莫奈的《睡莲》,孟克的《尖叫》,梵高的《星空》再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、达利的魔幻现实主义,博伊斯的行为艺术等等,逐渐的艺术越来越晦涩难懂。仿佛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,反而没有原始社会给予我们的价值更大了。
但至少在社会中,现代艺术给予人们的价值仍然受到认可,只不过读懂实在是需要太多的学习了,比如需要了解画家的背景、经历、画派等等复杂的因素。但是对于诗歌,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。特别是古代诗歌,我们大抵都忘却了怎么按照韵律和词牌名来作诗写词了吧。无外乎,在当今的实用主义的天下里,熊逸老师大为悲情的感慨:“我相信在今天最能得到广泛认同的答案是:什么都可以是诗,诗没什么用,诗人更没什么用。‘爱好诗歌’作为一种特质,在今天甚至含有贬义。”
诗歌洋洋洒洒千年,艺术风云变幻千载,两者虽然不同源,但也多少让人感到“同病相怜”吧。或许对于艺术和诗歌来讲,无论你看不看我,我就在那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