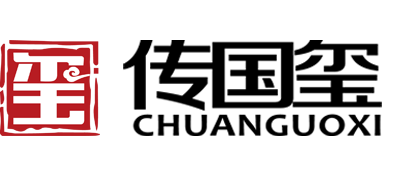莫名最近读完了熊逸版《王阳明》第十一章“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”,讲述他受到兵部尚书王琼重用,升任督察院左佥都御史,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等处(地域范围包含江西南安、赣州、福建汀州、漳州,以及广东、湖广若干市县),官阶处于中上,正四品,属于省级最高军政长官。在这期间王阳明发挥自己的才能,一举歼灭了在这里的四支叛军,名声大振。
在读这一章的时候,内心总是纠结的很。因为很难想象一个道德楷模,儒家的圣人会在战争之中使用欺诈的手段,而且在治理边患民众之时会使用“商鞅”的法家路数。我们站在现在可能对古代先贤都充满了敬意,觉得使用商鞅的法家学术没有什么,而且战争本来就是诡道,行军作战总是要靠“阴谋诡计”才能取胜的。
可是自宋代以来,儒家标榜的战争非但不是诡道,反而是正大光明的荣誉之道。所有儒家的大人物都对后来的“诡道”战争嗤之以鼻,特别是宋朝以来,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更是让大儒们看不起武将的“阴谋”。而商鞅更是被孔孟门徒所不齿,虽然儒家阵营里一直存在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之争,可是即便是推崇富兵强国的霸道一派,所推崇的也不过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汉武帝、唐太宗,谁都不愿提及甚至是堕落到法家的商鞅那里。而王阳明不仅公然使用“诡道”还利用法家的“连坐”和“十家牌法”(可以理解为保甲制度)来治理边民。
而这种种军功也成了后人诟病王阳明“假圣人”的切入口。在经典的《年谱》(王阳明弟子所著)和王阳明上奏皇帝的《浰头捷音疏》中对其中一个剿匪故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版本。
《年谱》中记载叛贼头目池仲荣受到感化,并受到王阳明的武力威慑,帅一干人等前来投诚,王阳明热情款待,很是大儒风范,不料被军中部下所逼,城中百姓所逼,不得不杀掉匪首,(动力网赚原创))还描述了他“当日无法下箸,晕眩呕吐”,为不能感化悍匪而深深懊恼。而《浰头捷音疏》王阳明叙述自己布置一切疑兵和缓兵之计并非感化悍匪,而是为了等待兵马就位,待到兵马就位,设宴款待池仲荣,出伏兵尽擒其党羽,各哨并进彻底荡平浰头各寨。而“疏”是对皇帝的书信,王阳明想必不会欺君。
这使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,里边记载了乔治·奥威尔对印度国父——“圣雄甘地”的一段中肯的评价:“在很大程度上他参与了政治,损害了自己的原则,因为政治的本质决定他不能脱离胁迫和欺诈”。
对于王阳明而言或许也是如此吧。所谓的有识之士,顾名思义就是保持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,不泯然于众,他们的思想却不能为同时代人所接受,即便是未来的很多时代都不被理解。但是他们若想有所作为,就必须拿出点“乡愿”精神,在自己原则之外寻找可以利用的法门。毕竟人们只会对胜利者歌功颂德…….。